87年我中师毕业分到村小学,遭初恋父母嫌弃,后来我成校长的女婿
"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'雪',不是山上的雪崩,而是她眼里的那片雪白。"
八七年盛夏,知了叫得震天响,我拿着一纸通知书,怔怔地站在县教育局门口。
被分配到瓦子坡小学的消息,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里,激不起半点水花。
那时候,农村学校条件差得很,砖房子少,土坯房多,教师待遇低,工资一个月才四十多块钱,连城里卖布的营业员都不如。
大中专毕业生谁不想方设法留在城里?我也不例外。
可人家有关系,我没有。
档案早就发了下去,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带着满心的郁闷,我收拾了行李,想着得先去见见小陈。
小陈是我初中同桌,大学毕业后在县百货公司上班,我俩从高中就开始偷偷谈恋爱。
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以后的事,但我心里一直把她当成未来媳妇看待。
那天,我闷着头就往小陈家走,一路上想着怎么跟她说这个消息。
小陈家在县城西边的干部宿舍,两居室的楼房,在当时已经是很体面的住处了。
她爸陈主任在县供销社当科长,她妈在邮电局上班,是远近闻名的"吃商品粮"的干部家庭。
到了院子里,陈主任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,凤凰牌的,当时满大街都是"二八"杠,这种带双梁的自行车可是稀罕物。
见了我,陈主任连头都没抬,只是淡淡地"嗯"了一声。
"小陈在吗?"我硬着头皮问。
"不在家。"他的声音冷得像冬天里打上来的井水。

小陈妈从厨房探出头来,围着条碎花围裙,上下打量我:"小三河,你被分到哪个单位了?"
"瓦子坡小学。"我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八度。
"那不是最偏远的穷山沟吗?"小陈妈脸色变了,扭头冲屋里喊,"小陈,快出来,有事和你说!"
从里屋出来的小陈,穿着蓝底白花的确良衬衫,烫着当时最流行的"学生头",短短的刘海下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。
看见我,她眼中闪过一丝惊喜,又很快暗淡下去。
我知道,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
"爸,妈,你们先聊,我和三河出去走走。"小陈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。
陈主任哼了一声:"早点回来,你舅舅一家要来吃饭。"
出了院子,小陈拉着我在街上默默走着,半晌才说:"分到山里去了?"
"嗯,瓦子坡。"
"那得多远啊,坐班车要两个多小时吧?"
"听说还得走一段山路。"我苦笑道,"那边连公共电话都没有。"
小陈没说话,只是紧了紧我的手。
当晚,我们在小公园的长椅上坐到了十点多。
回去的路上,她突然问:"三河,你会一直在那边教书吗?"
"应该会吧,除非有机会调回县城。"
"那得等多久?"
"听说至少得五年以上。"
小陈沉默了。
晚上十一点,小陈在巷口碰我,递过一封信,眼睛红红的:"对不起,我爸妈不同意。"

"不同意什么?"
"不同意我们继续下去。他们说......"
"说什么?"
"说乡村教师没出息,一辈子都得穷着。"她低下头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,"我爸给我介绍了供销社的一个干部儿子......"
夏夜的风吹过来,带着湿润的气息,却吹不散我心头的苦涩。
"你自己怎么想的?"我问。
她没有回答,只是把信塞进我手里:"三河,对不起..."
那封信我一直装在胸前口袋里,直到去报到那天,它还贴着我的心口,沉甸甸的,像压了块石头。
瓦子坡小学坐落在半山腰上,校舍是三间砖房加两间土坯房,操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。
教室里的窗户纸已经发黄,墙上贴着褪色的地图,有几处还被老鼠咬了洞。
李校长五十出头,个子不高,精瘦的脸上总是带着笑,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小扇子。
看我来报到,他放下手里的《人民日报》,忙着给我倒水,还亲自帮我搬行李。
"你就是新来的王三河老师吧?县里早就打电话说了。"李校长脸上堆满笑容,"欢迎啊,欢迎!"
他安排我住在教师宿舍,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,放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就没多少地方了。
"年轻人,来这是受苦了。"他满脸歉意,掏出一包"大前门"递给我,"条件简陋,一学期才五十多块补贴,比县城差远了。"
我婉拒了香烟:"李校长,没事,我不怕吃苦。"

嘴上这么说,其实心里还惦记着小陈的事,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教师宿舍是间土坯房,下雨天四处漏水,蚊子多得像打仗。
晚上睡觉要用蚊帐,白天上课被蚊子叮得浑身是包,还不能当着学生的面抓挠。
我住进去没两天,就听说学校要盖新房子,李校长跑了三年,终于从县里要到了一笔款。
看着施工队一点点把新教学楼的地基打好,他眼里闪着光,像个孩子似的高兴。
"三河,咱们的孩子,也得有个像样的学校。"他拍着我的肩膀说,"别看现在苦,只要咱们用心教,总有一天,这山沟里也能走出大学生。"
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叫做"使命感"的东西。
李校长为学校操碎了心,他自己住的房子比我们教师宿舍还破,下雨天要用三个脸盆接漏水。
可他从不抱怨,还经常自掏腰包给家境困难的学生买文具和课本。
开学后,我被安排带二年级,二十多个孩子,黑黑瘦瘦的小脸上写满好奇。
教室窄,桌子旧,有的孩子坐在用木板钉的长凳上,歪歪扭扭的。
可上课时他们眼睛亮亮的,像天上的星星。
第一堂课,我板着脸装严肃:"同学们好,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,王三河。"
底下静了一瞬,随后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原来他们觉得"三河"这个名字好笑,说我怎么能和河流一样。
我也忍不住笑了:"因为我出生的时候,我们村刚好通了三条水渠,所以爷爷给我取名三河,希望我像河水一样,能给庄稼带来生命。"

那天晚上,我拆开了小陈的信,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:"三河,原谅我的懦弱。祝你在山里一切都好。不要记恨我。小陈。"
我把信折好,放进了行李箱最底层。
李校长有个女儿叫李雪,比我小五岁,在县师范上学,平时住校,很少回来。
国庆放假,她来学校看父亲,细眉大眼,说话轻声细语,跟她爹完全不同。
第一次见面,她帮我批改作业,一丝不苟的样子,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师范时的模样。
"王老师,你教得真好,这些孩子作业写得工整多了。"她认真地说。
"哪里,刚来不久,还有很多不懂的。"
"我爸常在信里提起你,说你教得好,孩子们都喜欢。"她笑起来像冬日里的暖阳,"爸爸很高兴学校来了你这样的年轻老师。"
那年冬天,山里下了场大雪,足足下了三天三夜。
窗外白茫茫一片,村里的路都被雪封了,学校停课,我们几个老师凑在一起,围着炉子喝酒聊天。
周六下午,我正在宿舍批改作业,听见外面一阵喊叫。
李校长慌慌张张地跑来,脸色苍白:"三河,雪去山沟边上拍照,刚才有雪崩,她没回来!"
我二话不说,拿上手电筒就和李校长往山上跑。
天已经黑了,雪地反光,我们顺着一串脚印找去,远远看到李雪躺在结冰的水沟边,半个身子掉进冰窟窿。

"雪!"李校长大喊一声,脚下一滑,也栽了下去。
情急之下,我扯下棉袄当绳子,先把李校长拉上来,再救李雪。
她已经昏迷了,嘴唇发紫,浑身冰凉。
我二话不说,背起她就往山下跑,一路摔了好几跤,裤子都磨破了也不觉得疼。
那天晚上,我们三个人浑身湿透,冻得发抖,围着炉子一直烤到天亮。
"三河,我欠你一条命。"李校长红着眼睛说,"要不是你,我和雪都得交代在那儿。"
李雪高烧三天才退,病好后收拾东西准备回县城。
临走时,她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:"谢谢你救了我和爸爸。"
打开一看,是一首小诗,歪歪扭扭的字里写着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我的感谢。
最后一句是:"雪崩时,短暂的黑暗后,便是漫长的光明。"
这话莫名让我想起了小陈,心头的伤痛却已经没那么锥心了。
五年过去,我从一个懵懂的毕业生变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。
新教学楼终于盖好了,红砖灰瓦,四间大教室,宽敞明亮。
教室里换上了新桌椅,墙上贴上了彩色地图。
村里通了电,学校也装了几盏电灯,晚上再也不用点煤油灯批改作业了。
李校长比五年前更瘦了,头发全白了,却总是精神抖擞,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。
村里人都敬重他,称他为"李先生",有什么家长里短的矛盾,都来找他评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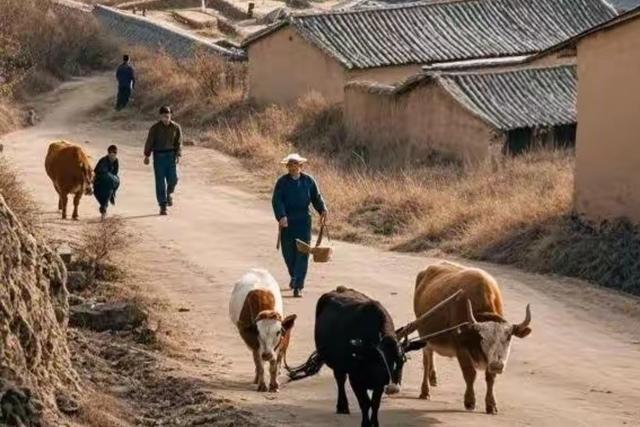
我也在村里站稳了脚跟,教过的学生考上初中的越来越多,李校长逢人就夸我。
"三河这娃子,是个教书的好料子。"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我也曾试着调回县城,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成功。
慢慢地,我也就不再强求,安心在瓦子坡教书。
偶尔回县城办事,会遇到以前的同学,他们大多已经成家立业,有的还当上了小领导。
而我,只是个乡村教师,人到中年,依然单身。
闲聊时,他们会说:"三河啊,听说小陈嫁人了,嫁给了供销社的杨科长儿子,日子过得挺好的。"
我只是笑笑,心里已经没有当初那种刺痛感了。
八年后,我已是教导主任。
李校长的头发全白了,背也有点驼了,却依然每天第一个到校,最后一个离开。
那年夏天,李校长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:"雪考上了省重点大学的研究生!"
"真厉害!"我由衷地为李雪高兴。
李雪回来看望父亲时,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,举手投足间有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。
她告诉我,自己选的是教育心理学专业,毕业后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。
。"她认真地说,"我想给他们做点什么。"
那晚,月亮很亮,我和李雪坐在学校的石阶上聊天。
她突然说:"王老师,你知道吗,我一直很佩服你。"
"佩服我什么?"
"佩服你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坚持这么多年,把最好的年华给了这些山里娃。"

我笑了笑:"没什么,习惯了。其实,是这些孩子给了我力量。"
李雪看着我,月光下她的眼睛亮亮的:"王老师,你从来没想过离开吗?"
我沉默了一会儿:"想过,但这里需要我。"
她轻轻点头:"我明白了。"
三年后,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:李雪拿着研究生文凭回到了瓦子坡。
乡亲们都很惊讶,读了这么多年书,居然回到穷山沟里来教书?
当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,站在新盖的教学楼前时,阳光照在她身上,仿佛带着一层光晕。
"你怎么回来了?"我吃惊地问她,"城里的学校不是给你留了位置吗?"
她笑了笑:"我欠这个地方太多。当年要不是你,我哪有今天?"
我心中一震,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夜。
"而且,"她继续说,"我想做的事,正好可以在这里开始。乡村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几乎是空白,我想从瓦子坡起步,慢慢推广到其他乡村学校。"
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,突然觉得她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我救的小姑娘,而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的年轻女子。
李雪回来后,给学校带来了新气象。
她开设了心理辅导课,教孩子们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,如何理解自己的情绪。
她还发动村里的青壮年修建了一个小图书室,从省城买来了许多书籍。
慢慢地,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多,甚至有邻村的家长专门送孩子来瓦子坡上学。

李校长高兴得合不拢嘴,每天哼着小曲在校园里走来走去。
有一次,他拉着我的手说:"三河啊,你看现在学校多好,比县城的小学都不差。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功劳啊!"
我笑着摇头:"是您带出来的好头,我们只是继续走下去。"
第二年,李校长退休了,我接任校长。
交接那天,李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:"三河,现在学校交给你了。我这辈子没做别的,就做了这一件事,把瓦子坡小学办好,现在看到你接班,我就放心了。"
我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泪来。
更让我意外的是,有天下午,办公室来了位客人,正是小陈的父亲陈主任。
十几年不见,他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,头发花白,脸上的皱纹像刻出来的。
见了我,他有些拘谨,进门就给我鞠了一躬。
"王校长,对不起,当年是我有眼无珠。"他叹了口气,"那会儿只觉得教师没出息,现在才知道,教书育人是多么崇高的事业。"
我忙让他坐下:"陈主任,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?"
"是这样的,我孙女今年上小学了,我想送她来瓦子坡读书。听说你们学校教学质量在全县是数一数二的。"
我有些惊讶:"您不是住在县城吗?送到瓦子坡来不是太远了?"
陈主任苦笑道:"小陈现在在县医院当护士长,嫁了个做生意的,日子倒是过得宽裕,就是两口子天天吵,孩子受了不少影响。我想让孙女来这里,一来读书,二来避避风头。"

我点点头:"行,学校欢迎每一个孩子。"
送走陈主任,转身看见李雪站在门口,眼睛亮亮的。
"怎么了?"我问。
"刚才那是你初恋女友的爸爸吧?"她笑着问。
我一愣:"你怎么知道?"
"我爸告诉我的。"她走进来,轻轻关上门,"他说,你刚来瓦子坡那会儿,每天晚上都偷偷看一封信,看完就叹气。"
我有些尴尬:"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"
"我爸总说,你是他看着长大的,现在比他当年强多了。"她浅笑着,靠在窗边,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身上,"三河,这些年,我一直......"
她没说完,但我懂了。
"十年前那个雪夜,你救了我两次。"她轻声说。
"两次?"
"第一次是把我从冰窟窿里拉出来,第二次是那首诗。"她眼中闪着光,"你可能不记得了,那首诗的最后一句是你写的,原稿被雪水打湿了一半,你帮我补全的。"
我想起来了,那句"雪崩时,短暂的黑暗后,便是漫长的光明"确实是我添上去的。
没想到她一直记着。
。"她向我走近一步,"我回来,不只是因为欠这个地方太多,还因为......"
她深吸一口气:"还因为我想和一个人一起,把这里变得更好。"

那天晚上,雪又开始下了,像十年前一样。
我站在教学楼前,望着远处的山影,心里踏实又温暖。
月光下,李雪站在我身边,我们的影子在雪地上拉得很长很长。
"三河,你还记得小陈吗?"她突然问。
"记得,但已经不会为她难过了。"我诚实地答道。
她点点头:"那就好。我不希望自己是任何人的替代品。"
我拉起她的手:"你从来不是谁的替代品。你是李雪,是你自己。"
远处的村子里,星星点点的灯光像天上落下的星星。
有些路,走得再苦再难,最终都会有花开的时候。
而我,终于在这山谷之中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雪原。